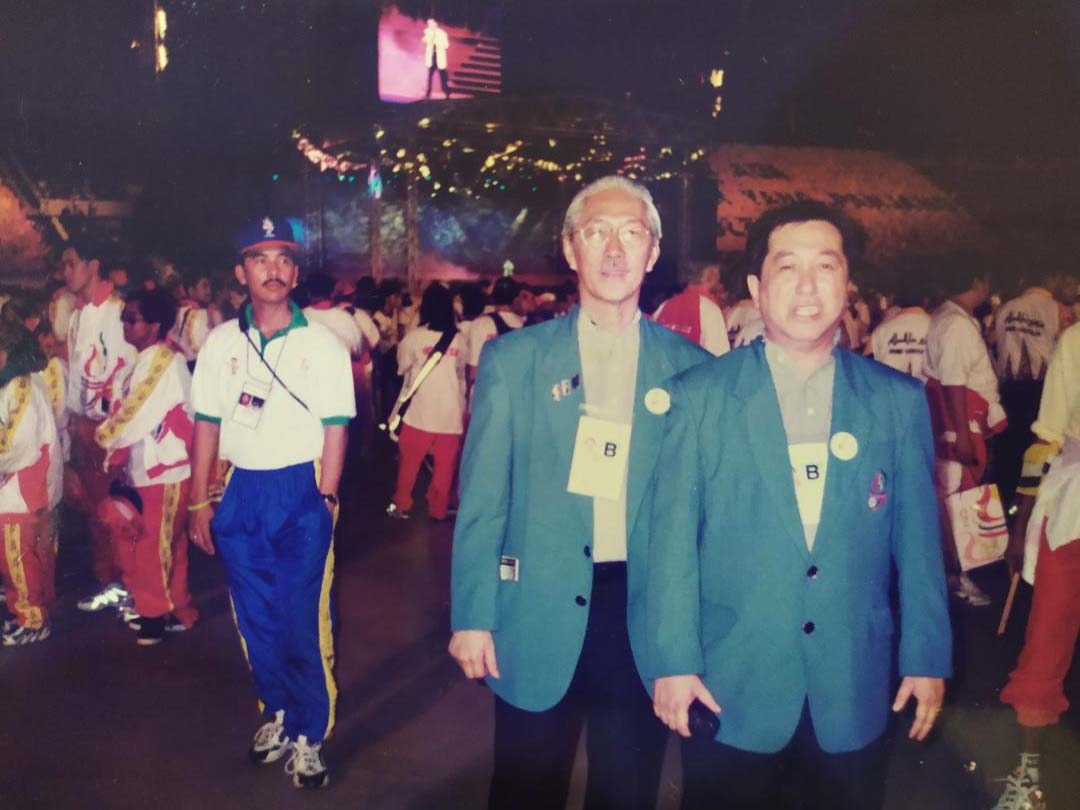从学生时代我就喜欢华文的写作,初中二开始就与同学西成经常写一些散文短词投稿到报社。在学校也获得华文课老师欣赏,经常将我的作文拿去贴堂,这使我对华文写作更有信心。
1963年高中毕业后,1964年到淡武廊培育学校当了一年的校长,由于同学们不鼓励我在乡下当老师,因他知道在学生时代我敢为学生的福利或相关事务到校长室理论或写“学府风波”,“读者之声”。
印象最深刻的是在高中三时候,曾与华文课陈老师为书中的解译,闹出轰动校园的事。事由每次上华文课前,我都会先阅读看有关的课文、参考书或查字典的解说,在某一节华文课时候,我站起来问老师“如果我这样解译是否行得通?是否与老师的解说殊途同归?”年少的我料不到学生希望与老师探讨书中的解说会使他大发脾气,并马上走出课室。
该名老师叫校长处罚我,如果没有处罚我,他将不来授课。但好在校长明了事理,冷处理这事,三天后,校长没有处罚我,而老师三天后终究还是回到教室授课,我也因此被同学们公认为遇事不平则鸣的性情中人。
由于不适合执教的刻板行政工作,在同学的意见之下,我辞去培育学校的工作。从1965年开始在美里华联日报、卫报与汶莱星光日报服务、1968年获得美里日报社长黄克芳欣赏我的文笔,及在报社的文章敢说、敢写的个性,则约我见面之时,与我签下合约,做该报记者兼广告员。
但不久后,由于与同事意见不合,1970年辞去该工作,同年应诗华日报老板刘会湘亲自到汶莱与我见面之约,并聘请为该报在汶莱创设办事处主任兼记者。
办事处设在斯市苏丹街裕源号内,在写新闻之际,并招睐新户口刊登广告。汶莱“诗华日报“的汶莱前身并设开明号户口。
约两年后我获拿督林鹏寿创设之马来西亚日报聘为汶莱负责人,并提供我办事处(设在中华商会二楼)及住宿。后来沙巴华侨日报也注意到汶莱的市场,其社长拿督叶宝滋及经理林玉真筹措汶莱分行时后,特邀我加入发展队伍,全权负责在汶莱市场开疆辟土的工作,当时沙巴华侨日报的办事处设立在斯市侨联大厦二楼。
因为对社会中我认为不合理的事务不愿妥协,凡见不公,必借笔为文,在各报发表,带起舆论的做法,获得社会大众肯定,这也引起美里日报董事成员的注意,1975年4月1日,美里日报社长黄克芳、董事长督谢晋新、副董事长丕显拿督林德甫拜访我,并诚聘我为该报汶莱办事处主任,统筹新闻采访、广告召睐工作后升为汶莱区经理。
丕显拿督林德甫当年在会面中用闽南话对我说“自己人为做自己的报纸”,在美里日报期间 因董事成员对我的能力完全信任,经常嘱我代表汶莱董事参加在总社进行的常务会议、董事会议和股东大会 。
由于成家后,了解收入对公司存续与发展的重要性,我对公司广告业务成长非常重视。
恰逢1975年开始,汶莱大兴土木,各种基础建设如雨后春荀萌发,吸引许多国外大企业到汶莱投资,汶莱各行各业都蓬勃发展,经济是前所末见的繁荣,无论是建筑材料、五金行、造砖厂、工程承包商、木材行、船务公司、汽车代理商、家电行等都纷纷涌现,百货公司实也随经济腾飞,民众购买力强,市场经济欣欣向荣,而报纸是当时各商家向民众传递资讯的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和方式,对报章投放广告需求因此水涨船高,而我在美里日报除了新闻采访外 也负责营业这一块业务,加上因采访工作及喜接交朋友的个性,与许多企业负责人等交情很好,因此逢节庆或商号新张、红白事, 这些朋友都选择我在报章上刊登广告。
因为这些朋友的广告支持和订阅,美里日报在汶莱报份销量的每日数百份升至每日数千份。我个人甚至囊括了80%的汶莱华文报的广告量,月营收经常达到4万元之数,可称美里日报成长的功臣而无愧。
我在美里日报的工作除了招收广告成绩获得报社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成员的赞赏外 ,在采访工作上也深获同事的肯定,因为当时通讯技术不甚发达,每天的新闻资料与图片需在第二天中午十二时前备妥,由报车带返美里总部排版,印刷。因此我常常在晚上加班,以便顺利把资料送到总部,尽快把新闻刊出。
在新闻之外,我也写社论或“读者之声”,更曾经于一次元旦特刊中,豪写十篇,刊出大版,这记录至今无人能破。当时我为了写这些元旦特稿,多次到林梦长屋拜访达雅酋长,收集资料和给他们收集的古董拍照。也曾与消防人员到森林拍摄火烧森林和灭火的镜头,亦写了篇汶莱渤泥时期的苏丹王国的历史报导。
通常每一名记者只需交一篇元旦特稿,而我却写了十篇,加上广告方面的成绩,正是因为这些突出表现,让公司对我很欣赏和重视。
美里日报是我在报界最后一站,在这期间因我也设了自己的旅行社,到了上世纪90年代,因经常带旅行团出国的需要,无法完全兼顾报馆的工作特向美里日报请辞,惟公司念及我对公司的贡献和广大且良好的人际关系,而开出报界前无古人,相信也后无来者的做法挽留我,为我保留职位、保留办公室、出国无需申批,每月还享津贴的待遇。这是对我年轻时候全心全意为公司的付出和打拼的一种肯定。
纵我近70岁才完全从报馆退休,但至今仍与报馆同仁保持良好联系,有些时候一些旧属也会在工作上咨询我的意见和协助,我也尽可能分享经验,让汶莱媒体专业顺应时代发展。
有很多历久弥新让我回忆的事,在报业同事里,最让我难忘的人是经常与我一起工作的“报车铁人”吴永良。
为了每天尽快把报纸送到汶莱读者手中,他每天凌晨4点前,就到印刷厂载报纸,五时赶到峇南河口。由于该处的渡轮6时30分才开动,为了争取时间,他必须雇小舟过河,每次都要把重迭迭的报纸从车上搬上小舟,过了河后,又把报纸一摞一摞的搬上河对岸的另一部车子,以接力方式,争分夺秒的把当天报纸经过七渡港关卡到诗里亚的泥泞路,送达汶莱各地。
有时候因意外没法通过小舟过河时,便只能无奈在峇南的渡轮前的小店喝早茶,等待渡轮过江,在70年代,美里到汶莱的陆路并没有像现在的平坦柏油路,当时除了一条在林中沿油管开设,一遇下雨便是大水坑和极易陷车的泥泞路外,便只能选择在海滩行驶,但海滩行驶又常会遇上整车陷入滩涂泥淖中,损失惨重的情形。但吴永良的无畏精神和遇事解决的坚毅态度,成功让报纸在决大部份时候,是顺利送到汶莱各地读者手中的。
第二位让我怀念之人是美里日报总编辑兼经理蔡士文。他是同事,也是老师。在报馆时候,教会我如何将拍了照片后,在暗房里从整卷菲林(摄相胶卷)中,剪下有曝光部份拿去冲洗(显影和定影),也安排我做新闻校对工作及其他有关出版、发行等知识的岗位,把我从一名原来只会写稿的愣头青年,培养成能独当一面的全能手。这一位谆谆教导,耐心指引的良师益友,不幸于澳洲逝世,依旧让我依旧感怀和想念。
我在美里日报工作后期(80年代末及90年代初),当时的总经理郑隆发先生则是另一位让我怀念之人。温文儒雅的郑隆发在许多方面都给我很大的发挥空间,他同时是一位能聆听职工意见的经理,也对报纸的发展投入很大的心力,会带动职工团结一致,为公司业务打拼。
我與美里日報的淵源(文柯忠佑)
Please login to join discussion